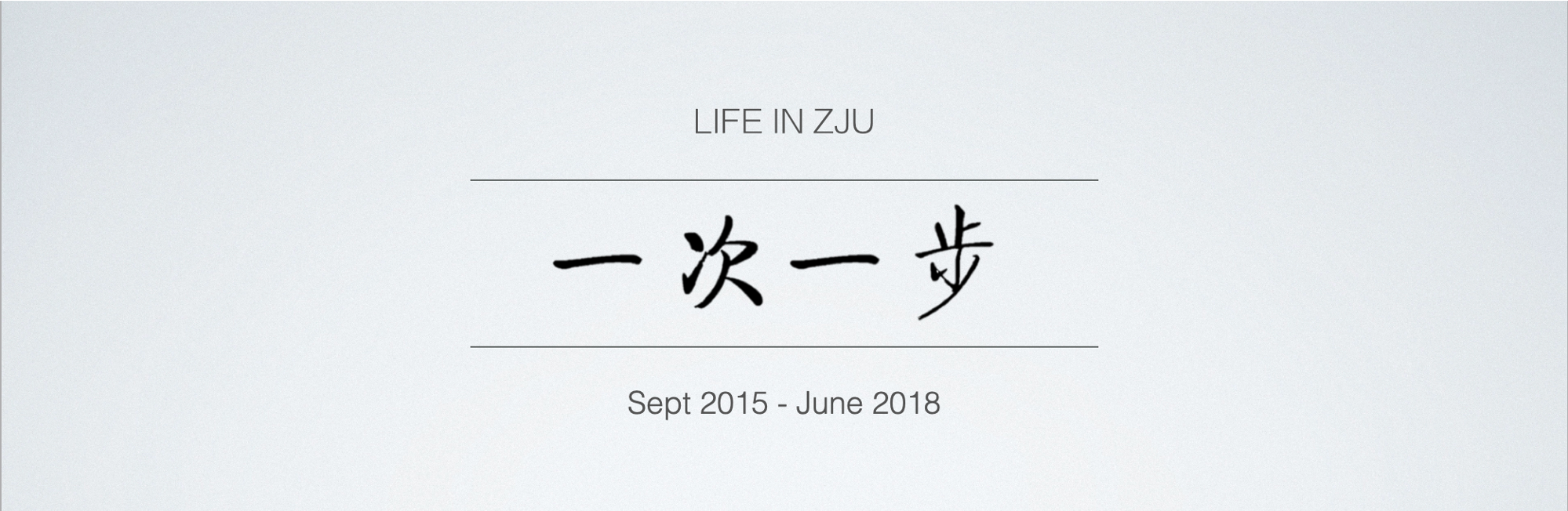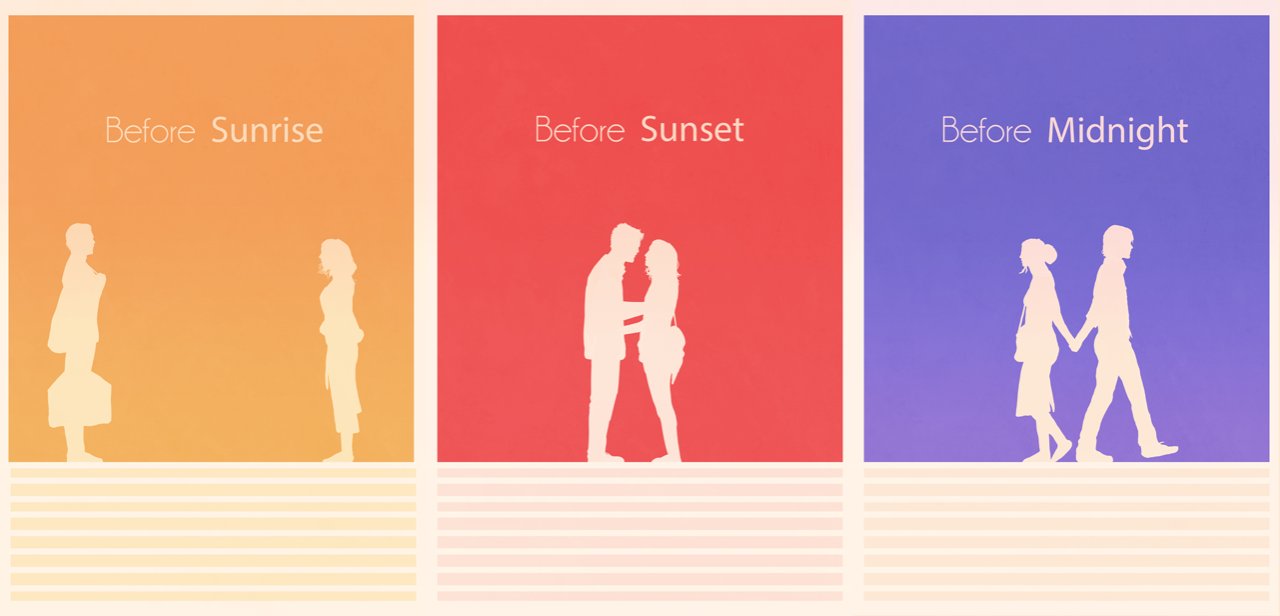关于生命的意义
从本科到现在写课程论文或研究报告通常都要提到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我一边捏造意义,一边怀疑自己捏造的意义。这样的小实验,可能自己过段时间都记不清实验细节与结论,距离真的对学术界做出贡献还路途遥远,最大的意义估计是论文中不敢写的获得学分与学位。不过换种说法就是在研究中锻炼了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等等,也算是意义吧。
做一件事情,如果你能喜欢,喜欢就是最好的意义,如果不是因为喜欢,那就得创造意义,因为任何一件事,有了意义感的附加,都会更容易被接受。
那生命的意义呢?弗兰克尔的《活出生命的意义》的德文原版最初叫做《不管怎样,向生命说“是”》,这是个很励志的标题,但我还是喜欢英文版的标题 Man’s Search for Meaning。因为追寻意义大概是人逃脱不掉的本性。
初级版意义:不让自己死于厌烦
先讲讲《罗洛·梅文集》(注:罗洛·梅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家)中的一个小故事吧:一天,美国布朗克斯的一名公共汽车司机开走了他的空车,直到好几天后才在佛罗里达被警察抓获。他解释说,由于厌倦了每天在同一条路线上行驶,他决定来一次这样的旅行。这个消息见报之后,他成了布朗克斯轰动性的人物,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到机场欢迎他的归来,公司也决定不对他进行处罚,而只让他保证以后不再做这样的短途旅行。
看到这则小故事,我先是不理解司机的举动,后是不理解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的举动。这不是一位公共汽车司机的“正常”行为,这样的行为又怎么会轻易被大众接受?罗洛·梅这样解释,司机的异常举动能获得社会大众普遍的同情是因为司机的行为代表了美国中产阶级某种相似的空虚感和无效感。人们之所以能够忍受这种千篇一律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偶尔地爆发,或者至少认同他人的爆发。但这种爆发,凸显的正是人们生活的无意义与荒谬。
这样的小故事算是生活中的“非常规事件”,但罗洛·梅的解释却不无道理,不过先把目光放到接地气的事例上,有两类内容在社交网络上很受欢迎,一类是对自己的梦想全力以赴的(例,伟大的安妮那“对不起,我只过 1% 的生活”的漫画曾引爆网络,在备受批评与争议之前感动了多少人),还有一类是希望获得内心平静的话(例,不久前被刷屏的网传为杨绛百岁感言又被辟谣的那段话)。这样一些内容的广泛转发似乎也在表明原来有这么多人希望自己的生活让自己更喜欢些,多些从自身出发的对自己喜好与自身情感的觉知与关注,而不是现在的样子。但改变生活现状是需要冒险的,如果没有更好,很可能就是更糟,维持现状是最稳妥的选择,但如果这样的选择只是用自身妥协外界,人就要面临缺乏意义感的空虚。
我觉得戴维·里斯曼《孤独的人群》里讲到的“外部导向的人”可以部分解释现代人意义感的模糊与丧失。
里斯曼认为,当今典型的美国人是“外部导向的人”,他不是寻求出人头地,而是寻求“适应”,他的生活好像受到了一个紧紧固定在他头脑中并且不断告诉他别人期望他如何做的雷达的指挥。这种雷达型的人从他人那里得到动机和指导,就像那个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多面镜子组成的装置的人,他能够作为反应,但却不能进行选择,他没有自己有效的中心。
其实,不仅是美国,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在欲望膨胀的时代,“外部导向的人”才是“正常人”。毕竟外界标准是衡量评判一个人的价值与地位的标尺,人是社会的动物,完全脱离社会去考虑问题无异于耍流氓,但只听从外界而无视自己,生活将是空虚而疲累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点,也许这个平衡点就是所谓的意义感吧。用罗洛·梅颇为风趣的一句话说就是“生活在一个焦虑时代的少数幸事之一是,我们不得不去认识我们自己。”
无论是现在的学习还是以后的工作,会有压力、困难和枯燥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我的态度就像以前写的那样:
“不论在哪里过着怎么样的生活都学会乐在其中,我不怕生活累一点,就怕厌倦了自己的生活。因为我觉得最糟糕的生活不是累,而是倦,所以当我发现自己有点厌倦某种生活的时候,我就会做点小改变。”
具体什么改变不好说,但至少可以避免让厌倦感步步走向无意义感、无聊与空虚。
高级版意义:究竟是谁问谁
文章开头提到的弗兰克尔是位人生经历颇为传奇的心理学家,他在纳粹时期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过着炼狱般痛苦的生活。妻子和父母都死于毒气室,他得以幸存。重获自由以后,弗兰克尔把自己的经历与学术结合,开创了意义疗法,写了《活出生命的意义》。
看到书名以为弗兰克尔对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会给大家一个回答,但事实上他很聪明,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对于这个问题,他非常狡猾的规避了代替患者回答。他说:“最终,人不应该问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相反,他该认识到,他自己才是被生命诘问的人。”根据弗兰克尔的观点,人应该对自己负责,生命在时时刻刻向你追问:你能给予你的生命什么。罗洛·梅对于存在感的分析有同样的意味,他表示:未经内心省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自我对于意义和价值的寻求应当是个体获得存在感的主要方式。
所以,对于生命的意义,是你在叩问生命,还是你的生命在叩问你,究竟是谁问谁?
其实我常常认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是种情绪的产物。因为只有当一个人不如意、心情低落的时候才会迫切的希望得到“生命意义”的解答。因此,换个角度来看,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或许不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而是“你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或“这个问题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一个人处于不如意状态或极端苦境中,正如弗兰克尔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对“生命的意义”有自己的答案是让他度过困境的至关重要的条件。正如尼采所言“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can bear with almost any how.)”但同时,没有人可以给另一个人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包括意义治疗家。“意义治疗家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一个画家,毋宁说是一名眼科医师。……而眼科医师则是要我们自己去看见真实的世界。……真理会自行呈现,无须他人干涉或居间介入。”
有时候我会觉得,如果这个时代“生病”了,那不是缺乏知识与技术,而是缺乏激情和承诺;如果一个人无法获得快乐宁静,无法自我认可和身心一致,那不一定是因为他拥有的太少,也可能是存在感的丧失和意义感的模糊。
“认识你自己”和“成为你自己”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真的要用一句话来回答生命的意义,那我选择这句话:“人生就是将各种问题呈现于个体面前,由他对这些问题做出反应。只有对自己负责才是对人生真正的解答。”